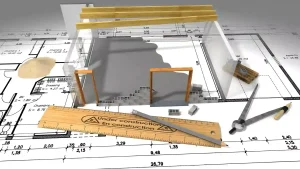葉家住在新北市一棟沒有電梯的舊公寓三樓,空間不大,隔間硬切,一家四口勉強擠著住。志凱出事後,每天上下樓都靠爸爸一手背上背下,已經這樣撐了一年。最近他們開始找透天厝、或至少是公寓一樓的房子,但預算不多。
餐桌剛好靠著走道,志凱的輪椅一半卡進桌底,一半還伸在外面。他沒說話,飯吃得慢,湯只喝了一口。新聞播著房市更新,他眼睛沒看,手機也沒碰,像陷進椅子裡。
葉金城一手端碗,一手拿筷,手臂還泛著背兒子的痠痛感。他沒抱怨,只偶爾用餘光看一眼兒子。
「妳今天練游泳的時候,有沒有配合節奏?不要只靠感覺喔。」陳麗娟語氣柔,聲音卻像針線縫得密。
珮甄咬著湯匙,點點頭,「教練說的,我都有記下來。」
「那下次我幫妳錄一下,回來自己對影片,這樣才會知道哪裡掉拍。」她話說得自然,手還在幫珮甄添飯。
志凱轉了一下輪椅,看向窗外,動作不大。誰都沒打斷媽媽說話。
「妳別想靠運動保送,游泳只是加分,考試還是必須及格,你看你哥……」陳麗娟講到這裡頓了一下,湯匙在碗邊敲了一聲。
「現在能用的手、能走的腿,妳還有,妳就要用得比誰都好。」她語氣沒高,但整張桌子都安靜下來。
珮甄沒說話,只是低頭扒飯,嘴角沒笑,背卻挺得比平常直。她知道媽媽沒在怪哥哥,可也沒真正放過那件事。
那是志凱高一升高二的暑假。
那天很熱,葉志凱揹著背包出門,說是去建梧家打電動。他說得輕描淡寫,媽媽也沒多問,只交代:「別太晚回來。」
建梧家住在郊區,是那種老透天,一樓有機車,鑰匙掛在牆邊誰都能拿。中午過後,他們吃完泡麵,坐在電風扇前吹了一會兒。
建梧突然盯著手機看了一眼,嘴角一翹:「欸,我女友剛傳訊息說,她跟閨蜜正在車站那邊逛街,我們從這裡騎車過去,二十分鐘就到了。」
志凱抬眼:「現在?」
「走啦!騎我爸那台車,很快。」建梧笑得輕鬆。
志凱一開始有點猶豫,「我媽以為我在你家打電動耶!這樣跑出去被發現,她跟我爸告狀,我會被揍……而且,我答應她不會再跟你一起偷偷騎車。」
「哎呦,葉志凱你是小學生喔?」建梧笑了,推了他一下,「你媽又沒有裝監視器,出去二十分鐘又不是逃家,別那麼膽小好不好?」
「你才是在吃奶!」志凱沒好氣地瞪了建梧一眼,最終還是跨上了後座。
建梧熟練地把鑰匙從牆邊勾下來。
引擎發動的聲音低低的,還沒上路兩人就笑開了花。轉出巷口時,建梧的手機還在震,導航開著,志凱坐在後座,手抓著後扶,太陽照在他腿上,熱得發燙。
他記得車子開得快,轉彎沒減速,下一秒——一台小貨車從對面衝出來。
撞擊那瞬間沒有聲音,只有車殼硬扯的破裂聲、輪胎急煞在柏油上的尖叫。
志凱醒來時倒在地上,耳裡有嗡嗡的風聲,腿毫無知覺,血溫溫地淌過腳踝,像有人在他身上倒了一壺水。
建梧送到醫院時沒了呼吸,臉上沒血,像睡著一樣。
志凱撿回一條命,但兩條腿——
急診室的燈光太亮,冷氣開得很強,椅子冰冷,走廊長得像沒有盡頭。
陳麗娟坐在長椅上,手裡握著手機,從接到警局來電那刻起,螢幕亮著又暗下,沒有人來得及回她訊息。
手還在抖,指節泛白。
醫生出來的時候,腳步很快,臉色沒有太多表情。他低頭翻著病歷,抬眼時聲音平穩:「病人生命跡象穩定,沒有腦傷,內臟也沒有大出血……但下肢粉碎性骨折,膝蓋以下保不住了。」
陳麗娟沒有站起來,只是慢慢抬起頭。她的眼睛沒紅,嘴唇沒顫,臉上什麼表情都沒有,像是一張白紙忽然被蓋上一個紅色的章,沒有預告。
「截肢?」她問了一句,聲音不是懷疑,只是確認。
醫生點點頭:「我們會馬上安排處理,請家屬簽字。」
她的手從包包裡抽出筆,簽字的時候沒有抖,名字一筆一劃寫得端正。醫生離開後,她把筆放回包裡,動作像是在整理某種習慣。
接著,她低下頭,背靠著冰冷的牆,雙手交握,靜靜坐著。
她沒有哭,只是一直坐著。鞋子尖微微翹起,膝蓋併得很緊,像是整個人只能靠這樣不動,才不會碎掉。
陳麗娟不是那種會當場大哭的媽媽。
她一直相信,事情總有辦法解決,計畫、準備、提前反應——她的生活就是這樣構成的。菜單排好、開銷記帳、考試時間表貼在冰箱門上,她甚至習慣把冷氣濾網更換日期標在日曆上。
有時候朋友會說她太計較、太緊繃,她笑一笑不回嘴。她覺得,世界不會給她太多退路,計較,是她能活得像樣的方式。
志凱小時候摔車、燙傷、牙齒斷,她從不哭,一手抱著孩子,一手還能找健保卡,問醫生:「縫幾針?會不會留疤?」
這次醫院叫她簽下那張截肢同意書時,她也是冷靜地簽。她知道醫生不會跟她討論其他選項,那是最理性的處理。
可她沒告訴任何人,那天晚上,她回到家,走進廚房,看見瓦斯爐旁邊有一只空碗,是志凱出門前吃泡麵留下的。
她站在原地看了那碗十秒。不是捨不得,而是無法接受——那個早上她才擦過的地板、那只碗、那副筷子,還有兒子留的湯渣,全都還在。只有他的腿,沒了。
她走進去,把碗洗乾淨,把瓦斯爐擦乾淨,把地板再拖一次,動作一如往常。她突然站在廚房角落,握著抹布,眼淚忽然掉了下來,沒聲音。
那股怒意,怎麼也壓不住了。
她恨。她真的恨。
恨建梧。
恨志凱明明說是去打電動,卻跟著建梧偷跑出去,恨他們年紀不大,卻膽大包天。
她恨那個已經死了的孩子。
半夜,她想起在醫院走廊的那一幕。
建梧的媽媽坐在椅子上,撕心裂肺喊著兒子的名字,連哭都哭不出形狀,只剩下空洞的聲音。那個畫面她到現在都忘不了。那天走廊上所有的燈都很亮,卻誰也沒說一句話。
她恨了一夜之後,發現無法再責怪一個死去的孩子。
那一夜,她坐在廚房的地上,靠著櫃子,沒有說話,也沒再掉眼淚。
那天開始,家裡的重力就改變了。
佩甄記得醫院的走廊味道消毒水味很重,媽媽臉色沒有變,爸爸話也不多。所有人都沒哭,只有她自己晚上回家後在房間裡,把小夜燈開著躲進棉被裡,不小心哭出了聲音。
她不是為哥哥哭,她只是很怕。
不是怕媽媽罵,也不是怕游泳的成績不好,而是……哥哥原本也是好好的,一樣出門、一樣笑,一樣說等等回家吃晚餐。
但回來的時候,就不一樣了。
她說不上來那是什麼感覺,只是每次出門,她都會下意識看一下地板——鞋子有沒有穿好、拉鍊有沒有拉、手機有沒有帶、走路會不會滑倒。
怕好好的,也會突然變不一樣。
她就是莫名的心生惶恐。
哥哥出事後的那半年,媽媽變了。不是變溫柔,而是變得不敢嚴厲。她不再動不動就數落珮甄的粗心,也不再為答錯一題而數落她個半小時。
所有的訓斥到最後,她只說一句:「妳不能有事。」
那句話聽起來很輕,卻比以前的每一聲責備都更重。
若找不到介紹人結識丹楓,請在社團多多交流。
→臉書社團
本文中使用的該字號為虛構字號,故事情節如有雷同,純屬巧合。